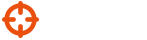曾参与拍摄央视纪录频道 CCTV9《Z世代青年说》,独立导演拍摄《Shakrs in a Changing Sea》,入围2025年罗利电影艺术节。
2024年6月,我从杜克大学的本校区搬家到了位于北卡罗来纳东部的海洋实验室,开启了第二年的研究生学习。
三小时车程,从达勒姆一路驶向莫尔黑德城(Morehead City),身旁的景色从高松树和橡树林,逐渐变成了扑面的海风与湿热的空气。
在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习之前,大家都说北卡森林资源丰富,适合徒步,却很少有人提到,这里是美国东部甚至于世界顶级的沉船和鲨鱼潜点。每年夏季,在几艘特定的沉船,都能看到沙虎鲨成群出现,成为了这里的明星物种。
作为潜水员,我很好奇:为什么北卡有这么多沉船?沙虎鲨又为何偏爱这些残骸?它们只在夏季聚集吗?当地潜水员是怎样与它们相处的?
带着这些问题,我联系了北卡州立大学(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)的Carol Price博士。她我讲述了一段关于社区、鲨鱼与科学的故事,而我用了一整年把这段故事拍成了纪录片。

每年8月30日是世界鲸鲨日。设立这个节日,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这种温和的“海洋巨人”的生存处境。鲸鲨隶属于软骨鱼纲、真鲨目、鲸鲨科,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。与庞大的身形不同,鲸鲨却以微小浮游生物为食,是一种滤食性动物。如今,它们已被列入IUCN 红色名录的濒危物种。
然而,不只是鲸鲨,全球的鲨鱼都面临相似的威胁:过度捕捞、误捕、栖息地丧失和气候变化,让它们的名字不断出现在IUCN红色名录之中。
和鲸鲨一样,沙虎鲨同样是一种“被误解”的鲨鱼。它们满口锋利的利齿,看似凶猛,却性格温和,对人类并无攻击性,并且展现出惊人的生存智慧。在2024到2025年间,我跟随当地的资深潜水员和科学家深入了解这个物种,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《Sharks in a Changing Sea》,讲述他们如何用一双双眼睛、一次次下潜和呼吸,默默积累起无价的海洋知识。
趁着世界鲸鲨日的契机,我想带你一起潜入美国东岸的北大西洋,把目光从“海洋巨人”转向另一群同样令人惊叹的存在——那些在沉船残骸间静静游走的“微笑鲨鱼”。


沙虎鲨(Sand Tiger Shark,学名 Carcharias taurus)广泛分布在全球热带和温带大陆架附近的沿海海域,从澳大利亚到南非,从日本到地中海,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然而,这种鲨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由于生长缓慢、性成熟晚、繁殖力低,以及分布范围与渔业高度重叠,它们极易受到过度捕捞和误捕的威胁。IUCN红色名录已将沙虎鲨列为易危物种,而在澳大利亚部分水域,甚至被列为极危。

在不同地区,人们还给沙虎鲨取了颇具画面感的名字:在澳大利亚,它们被称为“灰护士鲨”(Grey Nurse Shark);在南非,人们叫它们“斑点锯齿鲨”(Spotted Ragged-Tooth Shark)。光听这些名字,就能想象出它们满口尖牙、外表“凶神恶煞”的样子。但事实上,它们性格温和,对人类并无攻击性。
沙虎鲨在数百万年间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,被称为真正的“活化石”。它们在漫长的进化里积累了惊人的生存智慧:是唯一一种会主动吞咽空气的鲨鱼,把气体储存在胃里,从而能像潜水艇一样悬停,不必像其他鲨鱼那样不停游动才能呼吸。这种独特的“悬浮术”,让它们能够优雅地在复杂的沉船与礁体间缓慢穿梭。它们的牙齿也是生存的秘密武器:大约每8-15天就会更换一次,一生能掉落近三万颗牙齿。不断替换的锋利新牙,确保它们在捕食鱼类、甲壳类和鳐鱼时始终装备齐全。
沙虎鲨的繁殖方式是残酷的生存法则:在母体子宫里,最先孵化的胚胎会吞食其余同胞,直到只剩下最强壮的一只。成年后,雌性平均每年也只产下一只幼鲨,这是所有鲨鱼里繁殖率最低的之一。
正因为繁殖极慢,再叠加人类活动的干扰,沙虎鲨变得尤为脆弱,更需要我们的关注与保护。

在美国水域,沙虎鲨的分布范围从缅因湾延伸至佛罗里达,并进入墨西哥湾北部。由于种群数量下降,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(NOAA)已将其列为“关注物种”。自1997年起,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(NMFS)在《高度洄游物种综合渔业管理计划》中规定,在联邦水域范围内全面禁止捕捞沙虎鲨。

在这片漫长的海岸线上,北卡罗来纳(North Carolina)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区域。它位于美国东南部,大西洋西岸中段,恰好是墨西哥湾暖流与拉布拉多寒流交汇的地方。这种洋流的碰撞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,孕育了极高的生物多样性。但与此同时,复杂的水文条件、频繁的风暴与浓雾,再加上多变的浅滩和沙洲,使这里成为航海的险境。自殖民时期以来,无数商船和探险船在此触礁沉没,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这里又因潜艇战与海上交火而不断增加新的残骸。如今,已有超过两千艘船舶长眠于此,因此北卡外海被称为 “大西洋的坟墓”(Graveyard of the Atlantic)。

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,是二战期间沉没的德军潜艇U‑352。这艘VIIC型U艇于1940年在德国弗伦斯堡建造,1941年服役。1942年春,它从法国圣纳泽尔出发横渡大西洋,企图在美国东岸实施袭击,却于同年5 月9日北卡罗来纳外海被美国海岸警卫队驱逐舰Icarus投下的深水炸弹击沉。这是美国东岸首次击沉的德军潜艇。艇上15人遇难,33人被俘,余生都在战俘营度过。1975年,潜水员George Purifoy和好友通过翻阅史料和不断探索,终于在莫尔黑德城以南42公里的海底发现了这艘残骸。U-352静卧在 35 米深的沙质海床上,微微倾斜,却依然保持着完整轮廓。此后,George 在莫尔黑德城创立了奥林巴斯潜水中心( Olympus Dive Center),带领无数潜水员探索这片海域。如今,这家潜店由他的儿子Robert Purifoy 继续经营,已成为北卡最知名、最受欢迎的潜水中心之一。


二战期间沉没的德军潜艇 U-352 残骸,如今已成为鱼群与沙虎鲨的栖息地;声呐成像下,完整的船体轮廓依然清晰可辨。(图源:NOAA国家海洋保护区办公室 )
曾经象征死亡与战争的残骸,如今在海底成了新的生命绿洲。锈蚀的钢铁与断裂的木材,逐渐被藤壶、海葵与鱼群覆盖,小鱼藏身于缝隙间,中型鱼类追逐其后,而顶级捕食者沙虎鲨也在残骸间游弋。

这种转变并非偶然,而是一个正在被系统研究的新兴领域:沉船生态学(shipwreck ecology)。沉船为海洋生物提供了罕见的硬质基底,最初是微生物膜和小型附着生物“打底”,继而小鱼群和大型无脊椎动物加入,最终演替出复杂的食物网,吸引鲨鱼等顶级捕食者。而在辽阔沙底上,沉船则像一座座“海底驿站”,为鱼类和鲨鱼提供落脚点,让本来孤立的海域彼此联通。
但这个过程并非一成不变。金属缝隙里的化能合成细菌,会意外养活管状蠕虫等奇特生物;拖网经过时可能改变船体结构,让原本稳定的家园瞬间破碎;而金属本身也在海水与微生物作用下逐渐腐蚀坍塌,生态系统随之退化。
这些环环相扣的过程——从最初的演替和分带,再到生态连通性、能量流动、干扰和栖息地退化——共同塑造了沉船生态的动态平衡。

沉船并非静止的遗迹,它们在海底不断经历演替、分带、连通、能量流动、干扰和退化等过程,构成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。(插画:Alex Boersma)
在北卡外海,沙虎鲨直到 2000 年左右才在沉船区形成稳定聚集,这与沉船的材质和生态演替过程密切相关。早期沉没的木质船体在温暖、富营养的海域中,往往数年到十余年便被海水腐蚀或被微生物分解殆尽,难以维持长期立体结构;而二战时期的大量钢铁船体可在数十年至上百年间保持框架,既为藤壶、海葵等附着生物提供基底,又能承载更大规模的鱼类活动。二战沉船多在1940年代沉没,至1980-2000年间恰逢生态成熟期。而沙虎鲨偏好复杂的结构、丰富的食物来源和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,这些正是成熟钢铁沉船生态所能提供的。
因此,从20世纪80年代几乎难觅踪迹,到2000年后逐渐出现明显的聚集现象,正好符合沉船生态演替与沙虎鲨生态需求相互契合的逻辑。研究显示,部分雌性沙虎鲨会年复一年返回同一艘沉船。也因此,北卡的沉船不仅是鲨鱼的庇护所,也成了科学家的观测点。依托这些天然的窗口,研究者和潜水员共同建立了公民科学项目Spot A Shark USA,通过影像和长期监测,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“微笑的鲨鱼”。

截至目前,在北卡潜水员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,Spot A Shark USA数据库已经收录超过2800条沙虎鲨的个体记录。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,科学家逐渐揭示了沙虎鲨在沉船间的季节性利用、栖息地忠诚度和繁殖行为。这些成果在传统科研难以覆盖的领域填补了关键空白。更重要的是,这项公民科学项目动员了潜水社区的力量,让潜水员在贡献科学数据的同时,增强了对鲨鱼保护的理解与责任感。对于沙虎鲨这样易危的物种而言,这种科学与社区结合的力量,正是未来保护工作的关键。

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东岸,北卡罗来纳外海星罗棋布着成千上百艘沉船。它们曾经承载过宝藏与生命,却因风暴、浓雾、搁浅,或是战争的炮火,最终沉入海底。
百年之后,这些“海底遗迹”仿佛一座座庄严的教堂,在幽暗的海底重获新生。藤壶、海葵与各类无脊椎动物在船体上落脚繁衍,在原本荒芜的沙地上建起了层层演替的生态系统。这里,来自南方的墨西哥湾暖流与北方的拉布拉多寒流交汇,激荡起丰富养分,吸引小鱼聚集,中型鱼类追随其后,顶级掠食者沙虎鲨也随之而来。
从战争遗迹到生命绿洲,从科研空白到公民参与,沙虎鲨与北卡沉船的故事提醒我们: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割裂的。沉船见证了人类的历史伤痕,却在时间的洗礼下成为新的生态遗产;潜水员的快门与科学家的数据,共同汇聚成关于鲨鱼的知识网络。
在这个世界鲸鲨日,我们选择从沙虎鲨的视角讲述大海的另一种可能:即便是被误解的“微笑鲨鱼”,也在海底教堂中静静延续生命。希望今天的故事,能让我们在关注“海洋巨人”的同时,也更懂得海洋中无数生命与我们的紧密相连。
被误解的从来不只是鲨鱼,而是我们与自然之间尚未完成的对话。当野生动物悄然适应着人类的存在,我们是否也能学会在理解中与它们共存?
也许你此刻正好奇:为什么鲨鱼总被描绘成“冷血杀手”?北卡的沙虎鲨会根据季节选择不同的沉船吗?又或者,潜水员上传的一张照片,真的能改变它们的未来吗?
在这篇文章之后,我还将分享两篇相关的故事:下一篇会聊聊影像和媒体如何影响鲨鱼保护,我与真实鲨鱼同游的时候它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;最后一篇则带大家走进公民科学,看看人类与鲨鱼如何学会和平共处。
希望这三个小故事能连起来,让你对鲨鱼有一个更完整、更真实的认识。也期待你能和我一起,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海洋邻居。

本篇文章基于Lily在杜克大学的毕业论文,需要更完整的参考文献和学术细节,可以在这里查阅: